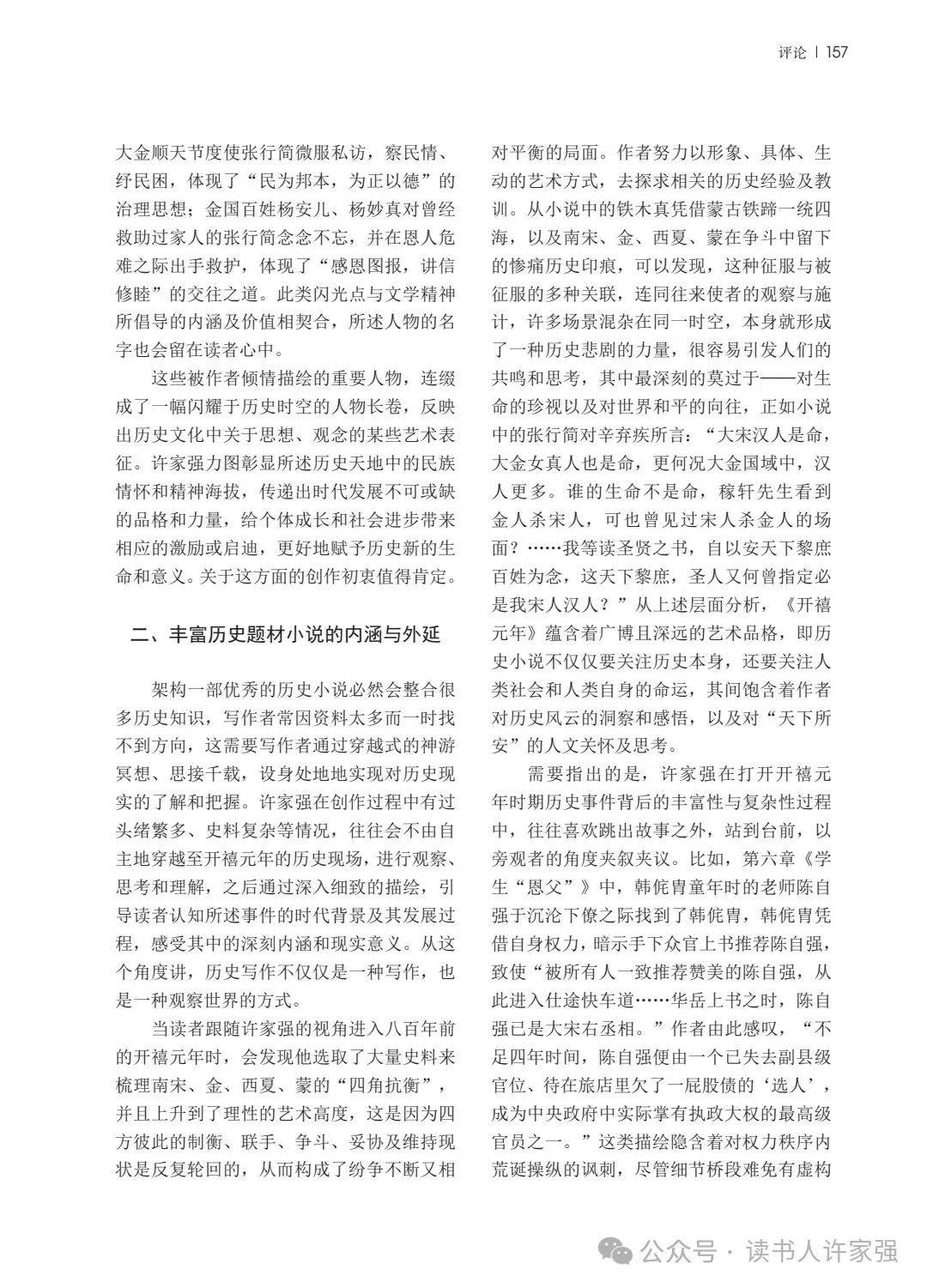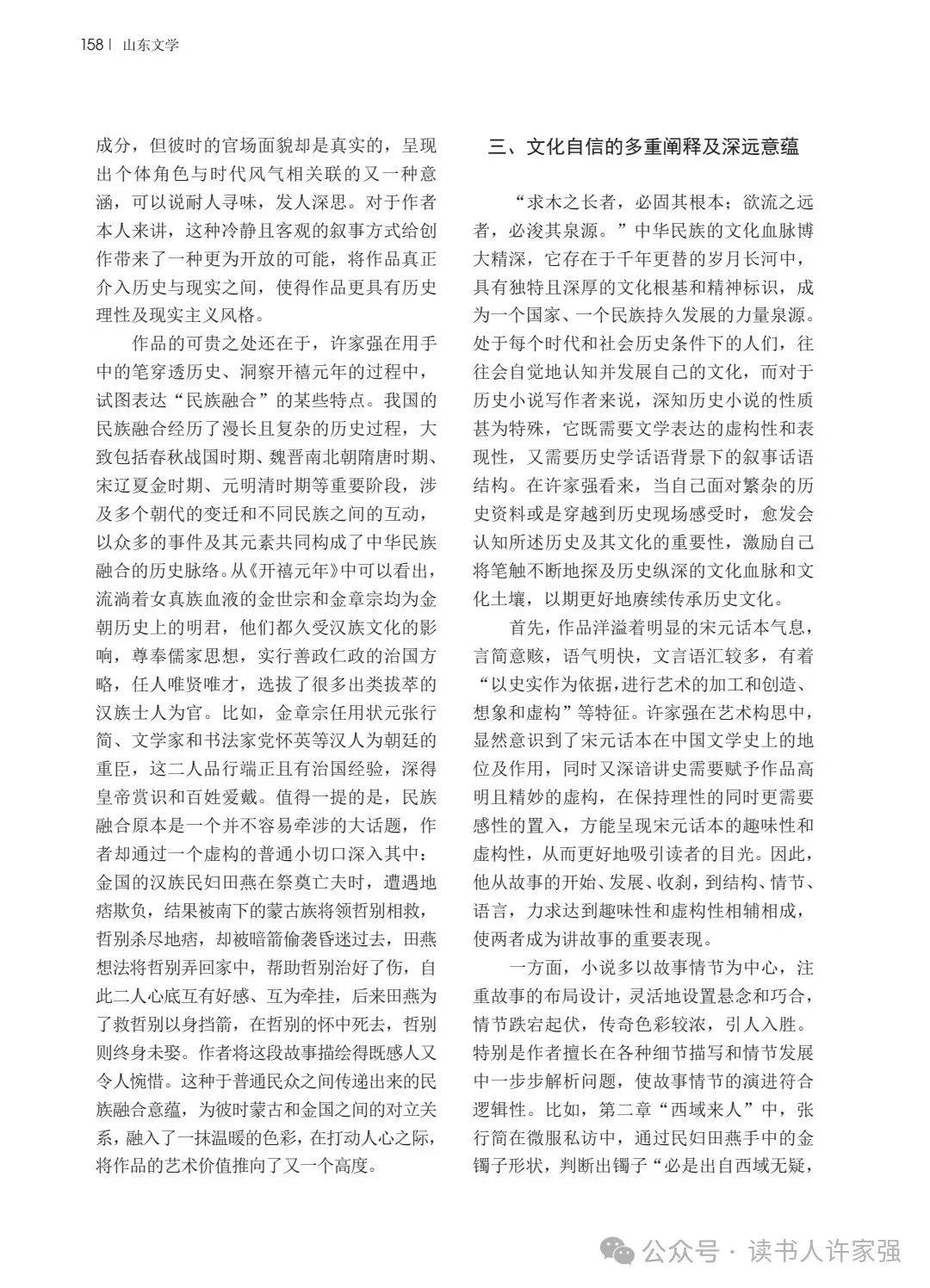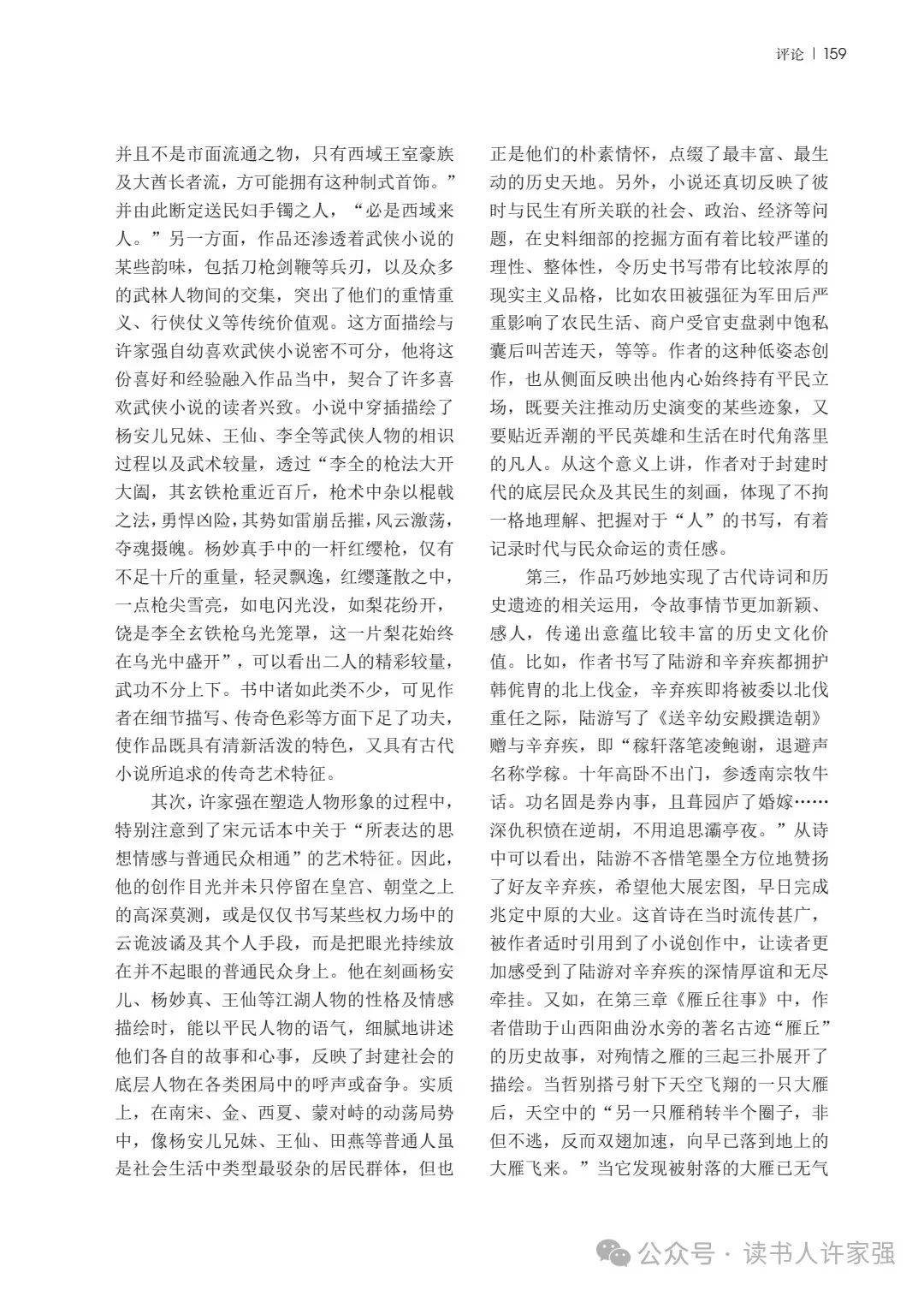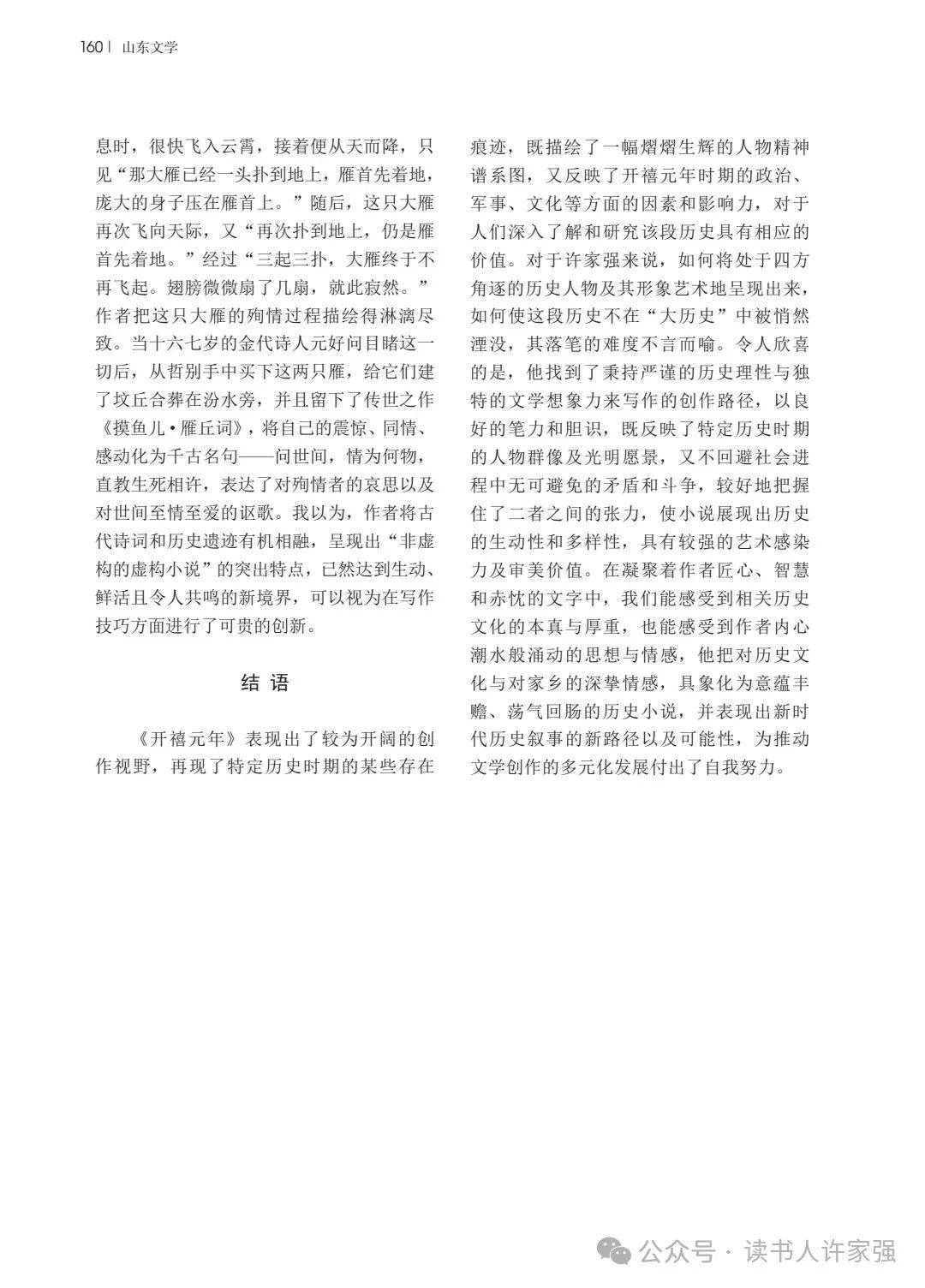中国作家始终葆有深厚的历史情怀,并将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感自觉转化到创作实践中,使得文学和历史呈现出如影相随的亲密关联。作为有着多年笔耕经验的小说家,许家强的小说世界里渗透着对历史的深厚兴致和不懈研究。他潜心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开禧元年》,紧紧围绕开禧元年的时代背景,着力描绘了处于该时期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背后的故事,以及对历史进程的深入解读,反映了对历史文化的赓续传承,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
在艺术表达层面上,《开禧元年》以基本史实为骨架进行虚构,叙事特异、构思精妙,在历史与文学的交融回响中,呈现出古今相通的人性共性,包含着对所述历史的研读与思考,旨在突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政治生活面貌。作者能够通过灵活多变、跌宕起伏的情节叙事,反映复杂且矛盾的社会阶段,同时又能以理性与激情的支撑,建构起虚实交加、大气雄浑的创作空间,展现重要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所具有的艺术特色。作品植入了许多文化底蕴和价值观,读者可以通过审美内涵及价值取向,进一步赏析历史小说的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继而正确地认知和总结作者笔下的历史。
一、具有传承意义的生存价值和精神取向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上,开禧元年不失为一处重要的时间节点,处于南宋、金、西夏、蒙并立时期,古今文学作品对这段历史鲜有触及。许家强自少年时期便对中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致,多年来始终葆有不懈的阅读与研究,他将创作目光聚焦于八百年前的开禧元年时期,将作品置于恢宏且纷杂的大时代背景下,以南宋北上伐金、蒙古征伐西夏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创作线索,结合悬念、细节、情感、冲突等诸要素,沿着相关的历史印迹追溯开禧元年的文化与历史,将历史真实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呈之于世,令读者更好地为了历史对象而共鸣碰撞。作品以张行简、辛弃疾、韩侂胄、哲别、杨安儿、杨妙真等局部历史中的风云人物为创作主线,在强调故事源自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将相关事件嵌入部分虚构情节中,有机串连起一系列具有传奇性质的历史故事,同时又以开禧元年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为中心,以期公正地表现这些历史人物,使得他们的命运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这些紧密相联的叙事结构和表达方式,创造了更为丰富精彩的故事世界,此类艺术效果离不开作者文学性的再现,以及书写真实历史的能力与水平。
每个时代、每个阶段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我们穿越历史长廊回望时,发现不同时期的重要人物有着不同的贡献,给历史文化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灵魂性元素。对于历史题材小说来讲,对历史灵魂的寻找与书写无疑是重要旨归,但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许家强在穿越八百年的历史视野中,观照“开禧元年的人物、社会、国家、历史”,包含时代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等多个主题,在众多的主题中,作者忠实地描绘了处于时代风云中的传奇人物,以比较强大的想象力构建出张行简、辛弃疾、杨安儿兄妹等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使这些处于开禧元年中的多元人物形象不乏生辉之处。尽管这些历史真实人物的年龄性别不同、性格气质各异,来自于不同阶层,生活在不同区域,但合在一起便勾勒出一组以人性光辉为核心概念的人物群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日照籍的金国状元张行简情有独钟,开篇便书写了张行简及其建立的日照文澜书院,表明“日照,文澜书院。这是莒州在大金国唯一一位状元张行简,为他的家乡子弟所建的读书之处。”当年回老家省亲的张行简,看到了当地父老带着他们的孩子,围着高中状元的文奎书院绕圈,“心中颇为感慨,当即决定,由自己出钱,另建文澜书院一所,便是义塾的形式,以最低的费用,开放招收本地乡民的孩子入院读书。有的家境特别贫寒的孩子,以及因为极低收费而产生的书院费用不足,都由张行简个人补足。”很显然,考取状元的张行简为家乡子弟树立了榜样,其支持家乡文教事业、造福乡梓的品格亦可见一斑。这位几近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传奇人物,在许家强的至诚笔意中重现于当代人的视野,这固然与他对历史的挚爱及创作激情有关,但更多的是他对日照地域文化资源给予重视和发掘,看得出,他力求让家乡的文化资源以及文学品质留下长久的记忆。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小说家,许家强之所以能够成就作品并展现小说的艺术品格,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从日照本土考出去的金国状元张行简身上找到了创作灵感,使其成为架构小说创意的重要历史人物。
然而,作者的创作目光并未局限于日照和大金,而是将笔触逐渐扩展至同期的南宋、西夏、蒙古(当时尚未建国)、大理以及西域、天竺等地,其间“有朝堂之上兴国灭国的谋略;有宫廷之内阴暗晦涩的血腥;有疆场之上金戈铁马的杀戮;有江湖之中义薄云天的豪壮;有草原之上万马奔腾的气魄;有沙漠之中隐忍呼啸的权诈;有暗室之内精明透彻的算计;有市井之间人声鼎沸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些浩大繁杂的社会图景中,作品在故事推进中逐渐解构正与邪、善与恶、情与仇、敌与我等情势的界限,力求突出个体的社会角色及其内在的生命求索,呈现自我生命的最大潜能以及人性该有的情怀。诸如,南宋将领辛弃疾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秉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大金顺天节度使张行简微服私访,察民情、纾民困,体现了“民为邦本,为正以德”的治理思想;金国百姓杨安儿、杨妙真对曾经救助过家人的张行简念念不忘,并在恩人危难之际出手救护,体现了“感恩图报,讲信修睦”的交往之道。此类闪光点与文学精神所倡导的内涵及价值相契合,所述人物的名字也会留在读者心中。
这些被作者倾情描绘的重要人物,连缀成了一幅闪耀于历史时空的人物长卷,反映出历史文化中关于思想、观念的某些艺术表征。许家强力图彰显所述历史天地中的民族情怀和精神海拔,传递出时代发展不可或缺的品格和力量,给个体成长和社会进步带来相应的激励或启迪,更好地赋予历史新的生命和意义。关于这方面的创作初衷值得肯定。
二、丰富历史题材小说的内涵与外延
架构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必然会整合很多历史知识,写作者常因资料太多而一时找不到方向,这需要写作者通过穿越式的神游冥想、思接千载,设身处地地实现对历史现实的了解和把握。许家强在创作过程中有过头绪繁多、史料复杂等情况,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穿越至开禧元年的历史现场,进行观察、思考和理解,之后通过深入细致的描绘,引导读者认知所述事件的时代背景及其发展过程,感受其中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讲,历史写作不仅仅是一种写作,也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
当读者跟随许家强的视角进入八百年前的开禧元年时,会发现他选取了大量史料来梳理南宋、金、西夏、蒙的“四角抗衡”,并且上升到了理性的艺术高度,这是因为四方彼此的制衡、联手、争斗、妥协及维持现状是反复轮回的,从而构成了纷争不断又相对平衡的局面。作者努力以形象、具体、生动的艺术方式,去探求相关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从小说中的铁木真凭借蒙古铁蹄一统四海,以及南宋、金、西夏、蒙在争斗中留下的惨痛历史印痕,可以发现,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多种关联,连同往来使者的观察与施计,许多场景混杂在同一时空,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历史悲剧的力量,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思考,其中最深刻的莫过于——对生命的珍视以及对世界和平的向往,正如小说中的张行简对辛弃疾所言:“大宋汉人是命,大金女真人也是命,更何况大金国域中,汉人更多。谁的生命不是命,稼轩先生看到金人杀宋人,可也曾见过宋人杀金人的场面?……我等读圣贤之书,自以安天下黎庶百姓为念,这天下黎庶,圣人又何曾指定必是我宋人汉人?”从上述层面分析,《开禧元年》蕴含着广博且深远的艺术品格,即历史小说不仅仅要关注历史本身,还要关注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命运,其间饱含着作者对历史风云的洞察和感悟,以及对“天下所安”的人文关怀及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许家强在打开开禧元年时期历史事件背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过程中,往往喜欢跳出故事之外,站到台前,以旁观者的角度夹叙夹议。比如,第六章《学生“恩父”》中,韩侂胄童年时的老师陈自强于沉沦下僚之际找到了韩侂胄,韩侂胄凭借自身权力,暗示手下众官上书推荐陈自强,致使“被所有人一致推荐赞美的陈自强,从此进入仕途快车道……华岳上书之时,陈自强已是大宋右丞相。”作者由此感叹,“不足四年时间,陈自强便由一个已失去副县级官位、待在旅店里欠了一屁股债的‘选人’,成为中央政府中实际掌有执政大权的最高级官员之一。”这类描绘隐含着对权力秩序内荒诞操纵的讽刺,尽管细节桥段难免有虚构成分,但彼时的官场面貌却是真实的,呈现出个体角色与时代风气相关联的又一种意涵,可以说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对于作者本人来讲,这种冷静且客观的叙事方式给创作带来了一种更为开放的可能,将作品真正介入历史与现实之间,使得作品更具有历史理性及现实主义风格。
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许家强在用手中的笔穿透历史、洞察开禧元年的过程中,试图表达“民族融合”的某些特点。我国的民族融合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大致包括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辽夏金时期、元明清时期等重要阶段,涉及多个朝代的变迁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以众多的事件及其元素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脉络。从《开禧元年》中可以看出,流淌着女真族血液的金世宗和金章宗均为金朝历史上的明君,他们都久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尊奉儒家思想,实行善政仁政的治国方略,任人唯贤唯才,选拔了很多出类拔萃的汉族士人为官。比如,金章宗任用状元张行简、文学家和书法家党怀英等汉人为朝廷的重臣,这二人品行端正且有治国经验,深得皇帝赏识和百姓爱戴。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融合原本是一个并不容易牵涉的大话题,作者却通过一个虚构的普通小切口深入其中:金国的汉族民妇田燕在祭奠亡夫时,遭遇地痞欺负,结果被南下的蒙古族将领哲别相救,哲别杀尽地痞,却被暗箭偷袭昏迷过去,田燕想法将哲别弄回家中,帮助哲别治好了伤,自此二人心底互有好感、互为牵挂,后来田燕为了救哲别以身挡箭,在哲别的怀中死去,哲别则终身未娶。作者将这段故事描绘得既感人又令人惋惜。这种于普通民众之间传递出来的民族融合意蕴,为彼时蒙古和金国之间的对立关系,融入了一抹温暖的色彩,在打动人心之际,将作品的艺术价值推向了又一个高度。
三、文化自信的多重阐释及深远意蕴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博大精深,它存在于千年更替的岁月长河中,具有独特且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标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持久发展的力量泉源。处于每个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往往会自觉地认知并发展自己的文化,而对于历史小说写作者来说,深知历史小说的性质甚为特殊,它既需要文学表达的虚构性和表现性,又需要历史学话语背景下的叙事话语结构。在许家强看来,当自己面对繁杂的历史资料或是穿越到历史现场感受时,愈发会认知所述历史及其文化的重要性,激励自己将笔触不断地探及历史纵深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土壤,以期更好地赓续传承历史文化。
首先,作品洋溢着明显的宋元话本气息,言简意赅,语气明快,文言语汇较多,有着“以史实作为依据,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创造、想象和虚构”等特征。许家强在艺术构思中,显然意识到了宋元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作用,同时又深谙讲史需要赋予作品高明且精妙的虚构,在保持理性的同时更需要感性的置入,方能呈现宋元话本的趣味性和虚构性,从而更好地吸引读者的目光。因此,他从故事的开始、发展、收刹,到结构、情节、语言,力求达到趣味性和虚构性相辅相成,使两者成为讲故事的重要表现。
一方面,小说多以故事情节为中心,注重故事的布局设计,灵活地设置悬念和巧合,情节跌宕起伏,传奇色彩较浓,引人入胜。特别是作者擅长在各种细节描写和情节发展中一步步解析问题,使故事情节的演进符合逻辑性。比如,第二章“西域来人”中,张行简在微服私访中,通过民妇田燕手中的金镯子形状,判断出镯子“必是出自西域无疑,并且不是市面流通之物,只有西域王室豪族及大酋长者流,方可能拥有这种制式首饰。”并由此断定送民妇手镯之人,“必是西域来人。”另一方面,作品还渗透着武侠小说的某些韵味,包括刀枪剑鞭等兵刃,以及众多的武林人物间的交集,突出了他们的重情重义、行侠仗义等传统价值观。这方面描绘与许家强自幼喜欢武侠小说密不可分,他将这份喜好和经验融入作品当中,契合了许多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兴致。小说中穿插描绘了杨安儿兄妹、王仙、李全等武侠人物的相识过程以及武术较量,透过“李全的枪法大开大阖,其玄铁枪重有二三十斤,枪术中杂以棍戟之法,勇悍凶险,其势如雷崩岳摧,风云激荡,夺魂摄魄。杨妙真手中的一杆红缨枪,仅有不足三斤的重量,轻灵飘逸,红缨蓬散之中,一点枪尖雪亮,如电闪光没,如梨花纷开,饶是李全玄铁枪乌光笼罩,这一片梨花始终在乌光中盛开”,可以看出二人的精彩较量,武功不分上下。书中诸如此类不少,可见作者在细节描写、传奇色彩等方面下足了功夫,使作品既具有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具有古代小说所追求的传奇艺术特征。
其次,许家强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到了宋元话本中关于“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与普通民众相通”的艺术特征。因此,他的创作目光并未只停留在皇宫、朝堂之上的高深莫测,或是仅仅书写某些权力场中的云诡波谲及其个人手段,而是把眼光持续放在并不起眼的普通民众身上。他在刻画杨安儿、杨妙真、王仙等江湖人物的性格及情感描绘时,能以平民人物的语气,细腻地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和心事,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底层人物在各类困局中的呼声或奋争。实质上,在南宋、金、西夏、蒙对峙的动荡局势中,像杨安儿兄妹、王仙、田燕等普通人虽是社会生活中类型最驳杂的居民群体,但也正是他们的朴素情怀,点缀了最丰富、最生动的历史天地。另外,小说还真切反映了彼时与民生有所关联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在史料细部的挖掘方面有着比较严谨的理性、整体性,令历史书写带有比较浓厚的现实主义品格,比如农田被强征为军田后严重影响了农民生活、商户受官吏盘剥中饱私囊后叫苦连天,等等。作者的这种低姿态创作,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内心始终持有平民立场,既要关注推动历史演变的某些迹象,又要贴近弄潮的平民英雄和生活在时代角落里的凡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对于封建时代的底层民众及其民生的刻画,体现了不拘一格地理解、把握对于“人”的书写,有着记录时代与民众命运的责任感。
第三,作品巧妙地实现了古代诗词和历史遗迹的相关运用,令故事情节更加新颖、感人,传递出意蕴比较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比如,作者书写了陆游和辛弃疾都拥护韩侂胄的北上伐金,辛弃疾即将被委以北伐重任之际,陆游写了《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赠与辛弃疾,即“稼轩落笔凌鲍谢,退避声名称学稼。十年高卧不出门,参透南宗牧牛话。功名固是券内事,且葺园庐了婚嫁……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从诗中可以看出,陆游不吝惜笔墨全方位地赞扬了好友辛弃疾,希望他大展宏图,早日完成兆定中原的大业。这首诗在当时流传甚广,被作者适时引用到了小说创作中,让读者更加感受到了陆游对辛弃疾的深情厚谊和无尽牵挂。又如,在第三章《雁丘往事》中,作者借助于山西阳曲汾水旁的著名古迹“雁丘”的历史故事,对殉情之雁的三起三扑展开了描绘。当哲别搭弓射下天空飞翔的一只大雁后,天空中的“另一只雁稍转半个圈子,非但不逃,反而双翅加速,向早已落到地上的大雁飞来。”当它发现被射落的大雁已无气息时,很快飞入云霄,接着便从天而降,只见“那大雁已经一头扑到地上,雁首先着地,庞大的身子压在雁首上。”随后,这只大雁再次飞向天际,又“再次扑到地上,仍是雁首先着地。”经过“三起三扑,大雁终于不再飞起。翅膀微微扇了几扇,就此寂然。”作者把这只大雁的殉情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当十六七岁的金代诗人元好问目睹这一切后,从哲别手中买下这两只雁,给它们建了坟丘合葬在汾水旁,并且留下了传世之作《摸鱼儿·雁丘词》,将自己的震惊、同情、感动化为千古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表达了对殉情者的哀思以及对世间至情至爱的讴歌。我以为,作者将古代诗词和历史遗迹有机相融,呈现出“非虚构的虚构小说”的突出特点,已然达到生动、鲜活且令人共鸣的新境界,可以视为在写作技巧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创新。
结 语
《开禧元年》表现出了较为开阔的创作视野,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存在痕迹,既描绘了一幅熠熠生辉的人物精神谱系图,又反映了开禧元年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和影响力,对于人们深入了解和研究该段历史具有相应的价值。对于许家强来说,如何将处于四方角逐的历史人物及其形象艺术地呈现出来,如何使这段历史不在“大历史”中被悄然湮没,其落笔的难度不言而喻。令人欣喜的是,他找到了秉持严谨的历史理性与独特的文学想象力来写作的创作路径,以良好的笔力和胆识,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及光明愿景,又不回避社会进程中无可避免的矛盾和斗争,较好地把握住了二者之间的张力,使小说展现出历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及审美价值。在凝聚着作者匠心、智慧和赤忱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相关历史文化的本真与厚重,也能感受到作者内心潮水般涌动的思想与情感,他把对历史文化与对家乡的深挚情感,具象化为意蕴丰赡、荡气回肠的历史小说,并表现出新时代历史叙事的新路径以及可能性,为推动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发展付出了自我努力。
作者简介:
李毅然,山东日照人,作家、文学批评家,现任日照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山东作家培训班学员。作品刊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山东文学》《百家评论》等多家报刊。曾获第六届日照文艺奖(文艺评论奖)。著有长篇小说《闪光的高原》。